身份与族群系列(五)
当族裔认同走出“我是谁”的私人命题,走进制度、叙事与行动的空间
文|之间博客
导语|从“我是谁”走向“我们是谁”
在这个系列的前四篇中,我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身份的形成、扭曲与重塑:从多族裔的共通挣扎,到华人自身的五种认同路径;从学校与社区对身份的构建,到青年如何用创造回应代际张力。
而在这一篇终章里,我们希望提出更进一步的提问:
身份,不只是个人经验;认同,也不该止步于内心挣扎。
我们是否可以,将这些破碎的、混杂的、边缘的经验,转化为共同的语言与未来的设计?
“多元文化”之后:我们为何仍被排除?
几年前,一家公立高中举办“亚洲文化周”,请了几位亚裔学生上台表演K-pop舞蹈,台下掌声不断。但第二天,王同学向校方反映:自己在历史课上提交关于《排华法案》的报告时,老师竟说:“你可以选一个更‘有趣’一点的主题吗?”
美国社会早已习惯了“多元文化”的口号。学校里的海报上写着“Celebrate Diversity”,企业官网挂上各种族笑脸,活动板上贴满“亚洲文化日”与“太平洋之夜”。
但在象征之外,真正的权力结构是否改变了?
– 谁来决定学校课程里该讲哪些族群的历史?
– 谁制定图书馆、医院、警察局的服务语言?
– 谁坐在市议会、教育局、基金会、规划委员会的决策席上?
当“多元文化”沦为装饰品时,它掩盖的不是偏见,而是参与权的缺席。身份的力量,从不只是认同,而来自于我们是否能影响制度、共塑未来。
华人如何从“避风港”走向“共建者”?
2023年,刘阿姨第一次站上市议会的公开发言台。她用不熟练的英文表达了对公交线路调整的担忧,因为那会影响她每天接孙子放学。她讲完后,台下并没有热烈回应,但有一位西语移民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说:“谢谢你讲出来。”
这是刘阿姨第一次发声,也许不会是最后一次。
长期以来,华人社区往往被视为经济上的“自力更生”典范,但在政策、公共事务与制度设计中,我们的声音常常缺席。
这其中有现实因素:语言门槛、历史创伤、身份焦虑、资源不对等。
但也有观念惯性:
– “我们顾好自己就好。”
– “政治太复杂,我们不懂。”
– “等下一代再说。”
然而,如果我们不在,谁来替我们说?
如果我们的孩子被定义、我们的社区被忽视、我们的叙事被消音——我们还要沉默多久?
“自保”是理解,但不该是终点。若我们能将这份稳固的生存力,延伸为制度的参与力,或许,“共建者”的角色并不遥远。
谁拥有“代表”的资格?
一次社区筹资会议上,一位年长义工悄声说:“怎么总是那个不会讲中文的小伙子代表我们?他懂我们吗?”
另一个年轻人听见了,轻声回:“我不会讲中文,但我从小在奶奶身边长大,我试着听得懂她没说出口的东西。”
每次选举、每场对话、每个议题,都会浮现一个敏感的问题:
谁有资格代表我们?
– 是讲中文的人?
– 是有移民背景的人?
– 是出生美国、但愿意学习中文的人?
– 是有相同血缘,但不同阶级、性别或政治立场的人?
身份政治从来不是“全体一致”,而是需要不断协商与承认差异的过程。
真正的代表,不是会说“我们华人都怎样”,
而是愿意倾听不同“我们”的声音,并带着这些多元的经验与视角,进入公共空间。
代表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责任——代人发声,也代人倾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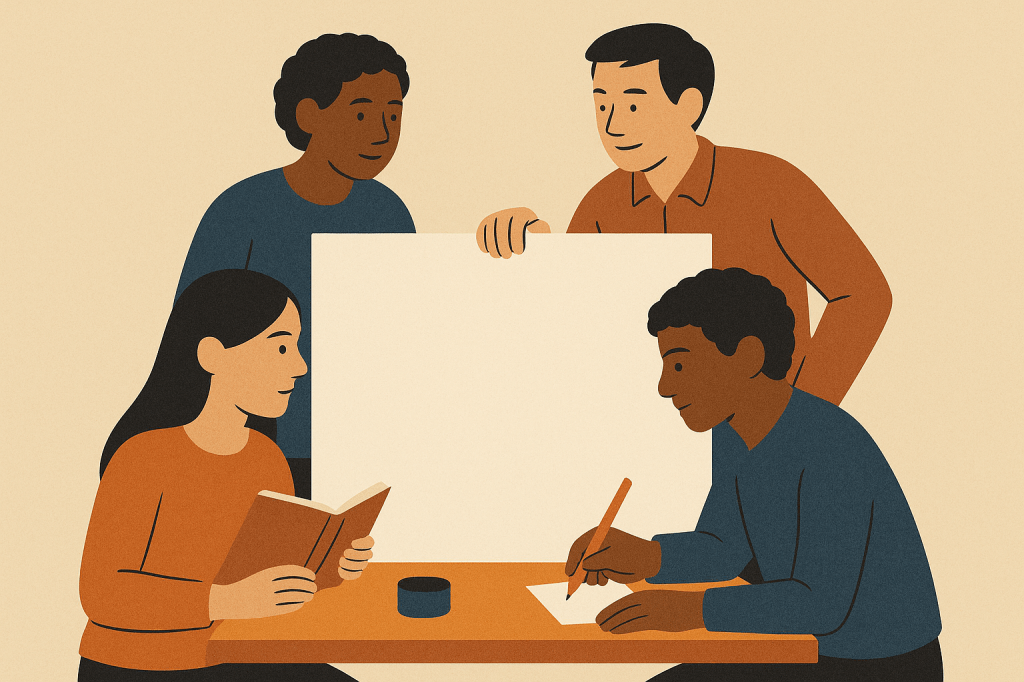
我们的共同未来,需要怎样的叙事与结构?
“我们也很努力”“我们很守法”——这类叙事,在某些场合有效,却也把我们困在一个“模范少数族裔”的陷阱中。
我们是否可以换一种方式讲述自己?
– 我们如何看待公共利益?
– 我们如何想象集体未来?
– 我们在资源分配、政策制定、文化表达中能否拥有平等机制?
比如,一位移民妈妈创办了“母语讲座”,让不懂英文的家长也能了解学校政策;
一群青年发起“双语预算读本”,帮助社区理解市政预算的每一笔支出;
有人尝试建立“文化联合提案”,让多个族群协作争取同一块社区资金。
这些都是在创造“新的结构”,在让身份变得不仅仅是标签,而是改变的起点。
我们的身份,从不是为了分裂,而是为了让这个社会能更真实地看见它的组成。
结语|结束不是终点,而是发问的开始
“身份与族群”系列写到这里,文字暂时告一段落,但提问与实践才刚刚开始。
如果你愿意思考“我是谁”,那我们也可以一起追问:“我们是谁?”
我们是谁的邻居?谁的同事?谁的选民?谁的父母?谁的创作者?
谁的制度设计者?谁的叙事参与者?
也许你曾在投票站前犹豫;也许你在朋友圈转发了一条关于语言权利的新闻;也许你只是参加了一场讲座,听到某人讲出你一直不敢说的话。
这些微小的片刻,就是我们在书写的共同未来。
我们要的是归属感,不是附属感。
未来,不该由别人替我们写好。
未来,是我们一起写出来的。
Discover more from 华人语界|Chinese Voices
Subscribe to get the latest posts sent to your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