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A「前世今生」续篇
在美国谈医疗改革,永远像是在讨论一个“理论上可解、现实中无解”的难题。前一篇文章里,我们回顾了 ACA 的历史路径,也拆解了它的制度结构。但如果要问:为什么 ACA 无法被彻底修复?为什么医保改革在美国几十年原地踏步?答案其实必须离开技术细节,走向一个更残酷却更真实的层面——美国医疗体系是一条政治经济链条,而不是一个可以靠技术修补的制度。
医疗价格是核心问题,而 ACA 从未触碰价格本身
美国医疗支出占 GDP 18%,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通常在 9%–12% 之间)。这不是因为美国人更常生病,也不是因为美国医疗技术遥遥领先,而是因为医疗服务价格比欧洲高出 2–3 倍,药价比其他国家高出 3–10 倍,行政成本占比全球最高,医院系统高度垄断,而私人保险的商业模式又依赖于“高价格–高保费–高溢价”的运作逻辑。
换句话说,美国医疗贵,不是因为“保险不够”,而是因为“医疗价格本身太贵”。在这样一个高价体系里,只要不触动价格本身,不管设计多少种保险形式,最后都会回到同一个问题:谁来为这套高成本结构买单。
而 ACA 做了什么?它做的事情本质上是:在不直接动医疗价格的前提下,通过补贴、税收抵免、监管市场的方式,帮助消费者在这个高价体系里“更容易买得起保险”,让一部分原本完全被排除在外的人,至少有机会拿到一张保单。
这就像是:房价上涨,你不是去监管房地产价格,而是发补贴让人“勉强买房”。短期似乎有效,个别家庭也确实因此跨过了门槛,买到了房子;但长期来看,房价如果继续上涨,补贴就不得不越发越多,财政负担越来越重,整个结构变得越来越沉重,却始终没有人真正去管“为什么房价如此之高”。
ACA 进入第十五年,本质上正陷入这个困局:它更多充当的是“高价体系下的财政缓冲机制”,而不是一套真正能够改变价格结构的“医疗改革机制”。
即便采用全民医保,美国也负担不起现有的医疗价格
很多人以为,只要有一天美国下定决心,转向“全民医保”或者“单一支付者”(single payer),问题就自然迎刃而解。但经常被忽略的一个现实是:即使换上单一支付系统,在不改变现有医疗价格结构的前提下,美国同样负担不起现在这套成本。
如果用一个粗略但直观的算术来衡量:美国医疗支出占 GDP 18%,而大多数实行全民医保的欧洲国家,医疗支出占比大致在 GDP 的 10%–12%。中间的差额大约是 6 个 GDP 百分点。如果美国希望把这部分开支全部纳入公共财政,就意味着联邦税收规模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增加 50%–70%。这是任何政治体系都难以承受的,更不用说对“加税”高度敏感的美国选民。
因此,问题从来不是“全民医保在理念上行不行”,而是在不触动医院、保险公司、药厂利润的前提下,其财政成本根本难以承受。若医疗价格与产业结构维持现状,单一支付者制度不过是把同样的高成本整体移至政府账上,不仅无法真正节省开支,甚至可能进一步放大财政压力,加速失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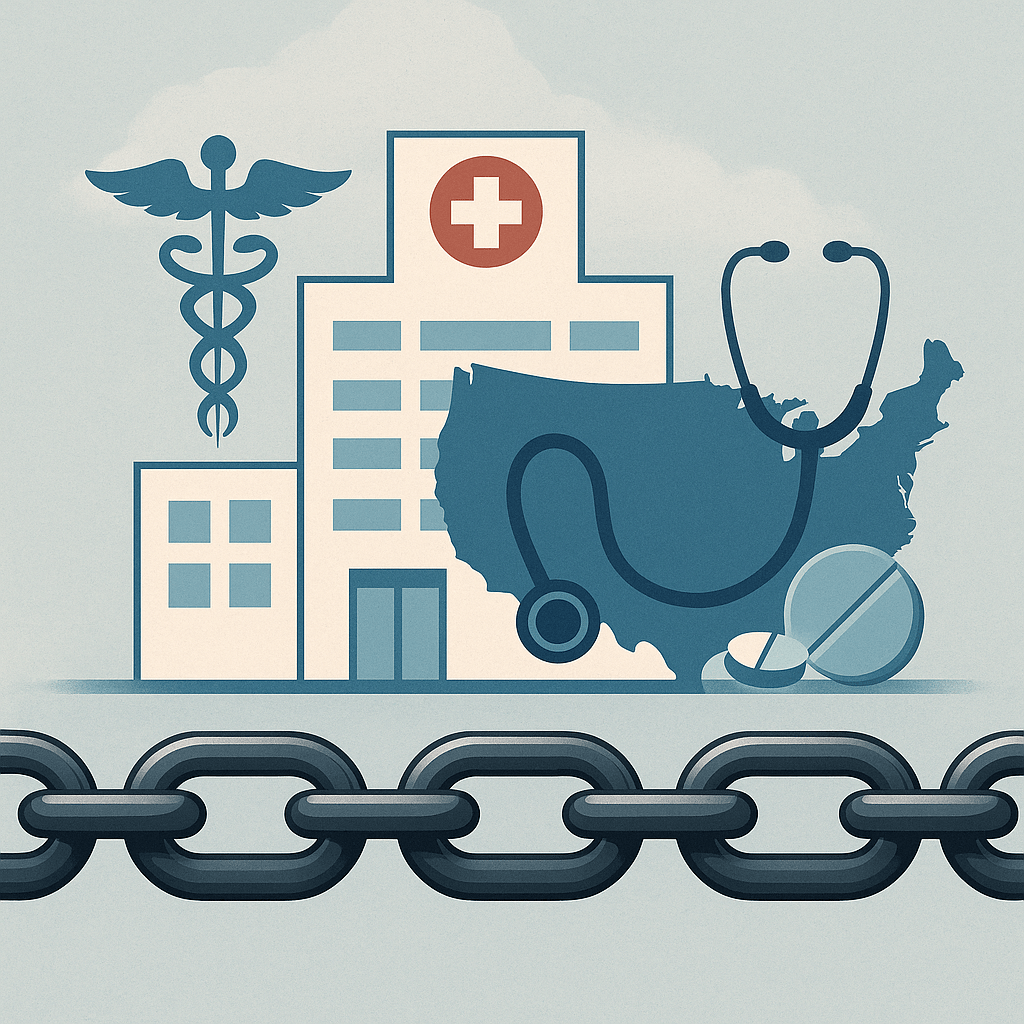
医院、保险公司、药企三大巨头——美国医疗的“铁三角”
要理解美国医疗价格为什么降不下来,必须先看清楚美国医疗产业的权力格局。过去二三十年里,美国逐步形成了以医院系统、保险公司、药企为核心的“铁三角”结构:
首先是医院系统。大规模的医院集团通过并购和整合,占据了许多地区的绝对优势地位,在很多城市和州,一个地区实际上只有一到两个大型系统可以选择,形成事实上的区域垄断。在这种格局下,医院对价格拥有极强的话语权,保险公司和雇主在谈判中处于相对弱势,“医院开价—保险买单—保费转嫁给雇主和个人”成为常态。
其次是保险公司。美国的大型商业保险公司,利润模式并不是建立在“治好更多病、控制住成本”之上,而是建立在“管理更大规模的保费池子”之上。保费越高、规模越大,管理费收入就越可观。这意味着,在现有激励结构下,保险公司对“真正压低整体医疗价格”的动力有限,反而容易通过设计高免赔额、狭窄医疗网络等手段,把成本更多地转移给患者。
最后是药企。美国的药品研发、生产和市场推广高度资本化,专利制度赋予创新药极大的定价权,再加上复杂的药品福利管理(PBM)体系、回扣机制以及缺乏全国性的统一议价平台,使得药企在定价上拥有极强的主动权。对于很多救命药或者慢性病用药,患者几乎没有议价空间。
医院系统、保险公司、药企这三方,在商业逻辑上高度一致:高价格意味着高保费、高溢价、高营收和高股东回报。“高成本结构”不是一个意外结果,而是这套产业体系天然倾向的状态。在这样的前提下,任何真正有力度的降价改革,都会被视为对整个产业利润基础的正面冲击。
三大巨头同时是美国两党最重要的金主之一
如果说“铁三角”解释了为什么医疗价格无法靠市场自身降下来,那么政治献金结构则说明了为什么美国国会在立法时几乎不可能真正触动这套体系。
医院往往是许多州和城市最大的雇主之一,既掌握当地就业,也掌握着医疗服务资源;大型保险公司和药企则通过全国性的游说网络和政治行动委员会(PAC),持续向两党候选人提供资金支持,影响立法议程的优先顺序。
对多数联邦议员来说,这三个行业既是自己选区的“支柱产业”,也是竞选连任时的重要金主。在这种结构之下,任何真正触动成本结构、削弱垄断地位、压缩利润空间的法案,在实际立法过程中都很容易被“修掉”“谈掉”“稀释掉”,最后变成一些象征性的透明度要求、有限度的试点项目,或者被塞进一堆条件之后悄然搁置。
因此,ACA为什么没有从根本上动价格?很大程度上不是技术上“想不到怎么改”,而是政治力量根本不允许你去改。医疗产业既是经济力量,也是政治力量。在现实的权力格局中,任何改革方案都必须在这三大巨头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做文章,而不是与之正面冲撞。
在有限政治空间里,ACA 的操作逻辑只能是:补贴 → 再补贴
如果价格动不了,利润动不了,垄断结构动不了,那么在现实的政治空间里,剩下能动的,几乎只剩下“谁来帮大家付钱”这一层面。这就是 ACA此后十多年里不断呈现出的逻辑:用补贴、税收抵免和公共资金,去缓冲一个自己无法改变的高成本体系。
在实践中,这种逻辑表现为一整套“财政缓冲工具”:增强版保费税收抵免让中低收入群体的月保费看起来没有那么惊人;成本分担减免(CSR)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部分投保人的自付额和免赔额;Medicaid扩张让最脆弱的人群不至于完全被排除在体系之外。每一项措施,单独看起来都在“改善可负担性”,也确实在统计意义上减少了无保险人数。
但问题在于:只要医疗价格本身维持在高位,这些缓冲工具就必须不断加码、不断续期。一旦补贴即将到期,账单立刻会以保费上涨、自付额增加的形式重新砸回到家庭头上。于是我们看到,围绕“要不要延长补贴”的政治争吵周期性上演,而真正关于“为什么医疗这么贵、价格结构能不能被改变”的讨论,却始终很难成为政治主流议题。
从这个角度看,ACA更像是一套“高价体系下的缓冲装置”,是让整个系统不至于立即断裂的安全阀,而不是一套可以带来结构性降价的改革方案。它确实改善了很多人的处境,但同时也把美国医疗体系锁定在一个“高成本–高补贴–高依赖”的均衡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医疗改革永远走不出原地
综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阻碍美国医疗改革走出原地的,并不是某一条具体的法律条文,也不是某一届政府的态度,而是一整套交织在一起的结构性现实:
第一,医疗价格被锁定在高位,形成一个以高成本为基础的产业生态;第二,医院、保险公司、药企构成了既相互依赖、又共同受益的“铁三角”;第三,这个“铁三角”同时又是两党立法者的重要金主,深度参与政治过程;第四,美国政治文化对“大政府”的普遍不信任,使得任何大规模集中支付、统一议价的方案在民意上都存在阻力;第五,在这种结构下,ACA所能做到的,往往只是通过不断扩大的补贴、税收抵免和公共支付,去延缓和缓冲高成本带来的冲击,而难以真正从根本上改变成本结构。
结果就是:ACA成了一场“半程革命”。它让最极端的医疗荒漠状态有所缓解,让数以千万计的人获得了某种形式的保险,也在统计数据上显著降低了无保险率;但与此同时,它并没有也几乎无力触动那条更深层的政治经济链条——那条由价格、利润、垄断和金主交织而成的铁锁。
结语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必要持续讨论 ACA 和美国医疗改革。因为医疗体系不是一个抽象的宏观问题,而是直接作用于工薪家庭的月度账单,作用于中产阶层的财务安全感,作用于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的生活质量,也作用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持续性和代际公平。如果不理解这条“政治经济铁锁”,我们就很容易把关于ACA的争论,误读成单纯的党派之争、技术之争,而忽略了它背后真正难以撼动的结构。
这一篇,作为《ACA的前世今生》系列的续篇,或许无法给出现成的解决方案,但至少可以把问题的边界画清楚:在一个医疗价格高企、产业利益根深蒂固、政治金主深度介入的体系里,所谓的“改革”,究竟能走多远,究竟是在修补制度,还是只是为一套难以为继的结构争取时间。
文|语间
Discover more from 华人语界|Chinese Voices
Subscribe to get the latest posts sent to your email.